当前位置:首页 » 深国交哲学社 » 正文
-
选自Giorgio Agamben: Sovereignty and Life, 2007, pp.11-22. 我很欣赏阿甘本的著作。我特别欣赏他惊人的古典学养,他在运用理论范畴时的直觉和分析的技巧,以及他把看似无关的思想体系联系起来的能力。但是,这种欣赏不意味着,我对他的理论结论没有保留意见。这些保留意见,是本文想阐述的。如果要长话短说,那么,我会说,阿甘本有美中不足之处(vices of his virtues)。读阿甘本的文字,人们常常有一种感觉,他还没梳理出某个词语、概念、机制的谱系,就急于确定它在当代语境中的效用。于是,在某种意义上,起源(origin)相对于后续事物有隐秘的绝对优先性。当然,我不是说,阿甘本天真地假定词源学(etymology)是后续事物的密码或线索。但是,我认为,很多时候他的论述在谱系解释和结构解释之间犹豫不决(undecided)。我们举一个索绪尔语言学的例子:拉丁语的necare(杀死)变成了现代法语的noyer(溺杀)。我们再怎么努力研究能指和所指关系的历时性变化,我们依然不能解释二者结合的意义:表意过程完全取决于某个价值(value)的语境。这个语境是独一无二的,是不能通过历时的谱系来把握的。这就是我们质疑阿甘本的理论路径的角度:他的谱系学不够关注结构的多样性,到头来有陷入目的论的风险。 
Giorgio Agamben / 图源:The New York Times 首先,我们看一看《神圣人》结尾的三个论点: 1. 原初的政治关系是禁止(例外状态作为外部与内部、排除与纳入之间的无区分地带)。 2. 至高权力的根本性活动是生产那作为原初政治元素的赤裸生命:赤裸生命是自然与文化、zoē与bios之间接合的界槛。 3. 今天,西方根本性的生命政治典范不是城市,而是集中营。 
我们先看第一个论点。阿甘本引用卡瓦尔卡的话:「禁止某人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伤害他。」正因为如此,神圣人可以被杀死但不会被祭祀。祭品是可以在城邦的法律秩序中再现的角色。强盗(bandit)的生命,清晰地表现出神圣人的那种外部性: 强盗的生命,如同神圣人的生命,不是同法律和城邦完全无关的一个动物性质的东西。它其实是在动物与人之间、自然与约法之间、排除与纳入之间的一个无区分界槛,一个通道性的界槛:强盗的生命是狼人的生命,他恰恰既不是人也不是兽,他悖论性地生活于这两者之中但又不属于这两者。
虽然主权是禁止的来源,但是,主权需要扩大禁止的适用范围。如果我们只应对狼人的法律的外部性,那么,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划分共同体的「内部」和「外部」。阿甘本深知内外关系的复杂性。因此,他在谈到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时说,它不是在盟约把主权交给利维坦之后随即消失的一种原初状态,而是共同体秩序内的一种持续不断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共同体被认为「好似被解散了」(tamquam dissoluta)的那一刻出现。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状态不是纯粹的、前社会的自然,而是始终指涉社会秩序的「自然化」,除非社会秩序失效。这就解释了例外状态是如何出现的。施米特认为,适用于混乱状态的法律是不存在的。一旦法律秩序与更广泛的共同体秩序之间的一致被打破,我们就需要例外状态。 自然状态远不是同城邦与法律完全无关的一个前司法状态,而是例外,以及是那构成例外并居于其内的界槛。与其说它是一场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不如更确切地说它是这样一种状况:对每个人来说,其他每个人都是赤裸生命和神圣人,都是狼人。这种人的狼化和狼的这一人化,在例外状态所开启的公民性之消解(dissolutio civitatis)中每时每刻都有可能。独独这一既非简单的自然生命,又非社会生活,而是赤裸生命或神圣人的界槛,总是在场,永远是主权之操作的预设。
正因如此,霍布斯认为,至高权力的基础并不在于臣民自愿放弃他们的自然权利,而在于主权者保留他可以对任何人做任何事的自然权利,即如今的惩罚权利。
因此,禁止把赤裸生命和主权结合起来。阿甘本认为,我们必须指出,禁止不仅仅是制裁——这样的话,它依然可以在城邦的法律秩序中再现——而且涉及弃置(abandonment),涉及神圣人,涉及其他排除在共同体秩序之外的角色。正因为如此,他们可以被杀死但不会被祭祀。在这个意义上,禁止是非关系性的:受害者陷入隔绝(separatedness)之中。在阿甘本看来,禁止是与主权有关的原初的政治关系。它比起外国人的外来性(extraneousness),要更为原初: 我们必须学着在诸种我们仍身处其内的政治关系和公共空间中去识别禁止的这一结构。在城邦中,神圣生命的放逐比一切内部性更为内在,比一切外来性更为外在。
因此,禁止是至高权力的来源。从一开始,把公民简化为赤裸生命的例外状态(阿甘本想到的是福柯的生命政治)就决定了现代性。 毫无疑问,阿甘本用禁止这一范畴,指出了政治的某些关键因素。在政治内部,当然存在一个否定性的时刻,它要求我们建立内/外关系,要求主权在法律秩序面前保持一种模糊的立场。可是,问题在于:阿甘本思考禁止结构的这些维度,是不是穷尽了禁止结构的可能性?换句话说,阿甘本是不是只选择了各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并且信以为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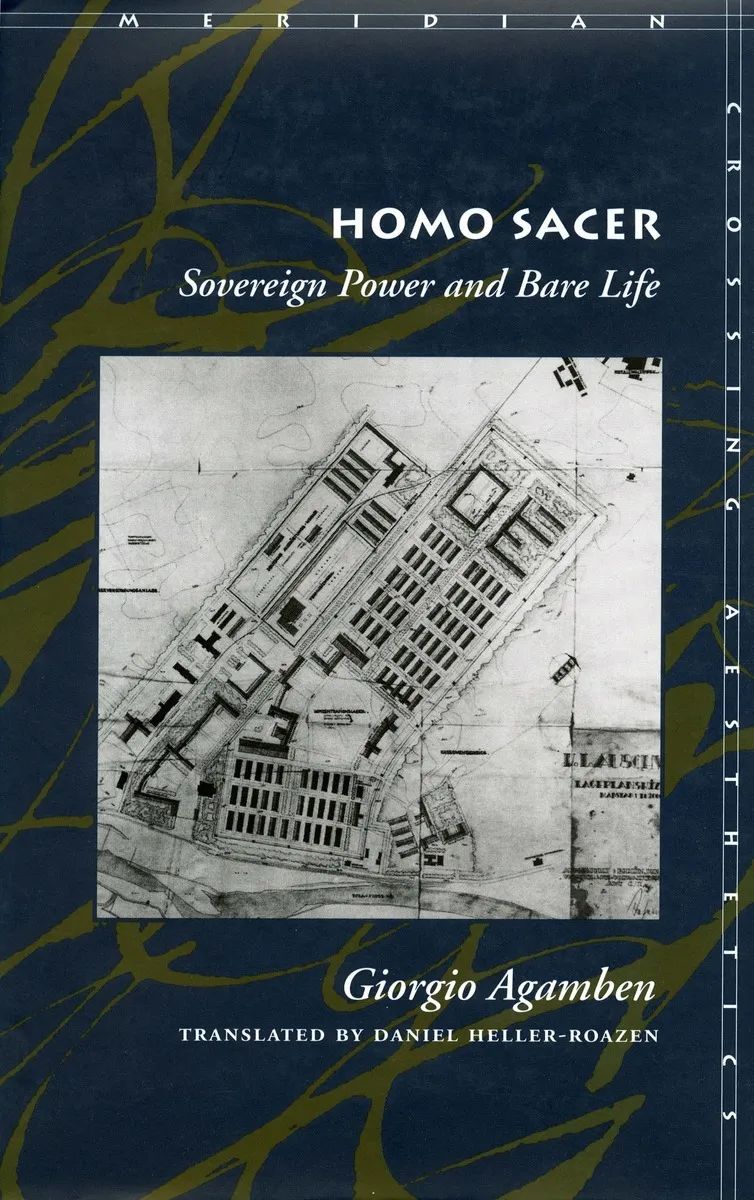
Homo Sacer / 图源: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我们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禁止的本质在于它的后果——也就是说,把某人排除在构成法律秩序的差异体系之外。但是,正如阿甘本所说,为了把「法外」(outside the law)的所有处境等同于神圣人的处境,我们还需要加上额外的预设。首先,与外界的全然隔绝,意味着这个人是赤裸的个体性,被剥夺了一切集体身份。其次,城外之人的处境,是彻底的毫无防备,全然暴露在城内之人的暴力面前。唯有在这种代价下,至高权力才是绝对的。可是,这两个额外预设是合理的吗?「法外」这一范畴从逻辑上能推出这两个预设吗?显然不能。城外之人不是被排除在「一切」法律之外。「法外」这一范畴仅仅意味着,被排除在「城邦」的法外。弃置不过是城邦的行为。我们不妨看看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的一段话: 如此被构成的游民无产阶级,并对城市的「安全」形成沉重的压力,它意味着一个无可救药的腐败,和深植在殖民统治心底的坏蛆。于是,拉皮条的、流氓、失业者和普通罪犯就像坚定的劳动者那样,从下而上的投入解放斗争。这些无所事事的、失去社会地位的人,通过军事和决定性的行动,重新找到国族的道路。他们在殖民社会乃至支配者的道德中,都不能找回自己的尊严,现在恰恰相反,除了通过手榴弹和手枪的力量,他们没资格进入城里。这些下三滥和失业者面对他们自己和面对历史,重新找回了尊严;妓女也一样,年薪两千法郞的女佣,绝望的妇女们,所有那些在疯狂和自杀间徘徊的男男女女,开始前进,并坚决的参加觉醒起来的国族大行进。
在这里,我们看到被排除在城邦法律之外的行动者。虽然他们不能纳入城邦法律的任何范畴,可是,这种外部性是对立于城邦法律的新的集体身份的起点。它不是对立于法律的无法(lawlessness)。在这里存在的,是互不承认的两种法律。在《例外状态》中,阿甘本讨论了意大利法学家珊提·罗马诺的「必要性」概念。他认为,在罗马诺看来,革命力量——按照国家法律秩序,被排除在法律之外——创制了自身的新法律。阿甘本引用了罗马诺的一段话: 所谓革命是反法律的(antijuridical),对于它所朝向对抗的国家实证法而言才是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从其定义自身的不同观点出发,它不是一个由它自己的法所命令与规制的运动。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必须被归类到原初法秩序的范畴中的秩序,在这个说法如今已经广为人知的意义上。就此而言,并且在我们所已经指出的范围之内,我们因此可以谈论一种革命之法。
因此,我们看到两个互不相容的法律。阿甘本的禁止概念中,依然有效的是「不可纳入的外部性」这一观念。但是,这种外部性的适用范围大大超出了神圣人这一范畴。我认为,阿甘本没有看到可纳入/不可纳入、内/外的真正普遍性。事实上,两个对立的法律的相互禁止(mutual ban),恰恰是任何彻底的对抗(radical antagonism)的性质——彻底的意思是,两个对立面无法简化为双方都承认的任何超级游戏(super-game)。 我认为,只有禁止是相互的,我们才有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关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社会力量的不断碰撞,才会有社会纽带的不断的争论和重塑。如果我们回到阿甘本对霍布斯的分析,就很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正如上文所说,不同于契约论的观点,阿甘本认为「主权者保留他可以对任何人做任何事的自然权利」——也就是说,臣民成了赤裸生命。可是,这两个维度的对立,是不成立的:主权者想要保留他的自然权利,需要得到其他臣民的承认,而这种承认,存在一些限制。 惩罚权利这个特殊状态,采取如下形式:自然状态在每个国家之心脏处存续。同这个惩罚权利状态对应的则是,臣民虽不违抗,但会抵制加诸在他们自己身上的暴力的能力,「因为……没有人应该被契约束缚而不反抗暴力。因此,没有人会故意把任何权利交给另一个人来把暴力加诸在他自己身上」。至高暴力事实上不是建立在合约上,而是建立在赤裸生命在国家中的排除性纳入之上。
阿甘本用「抵制暴力的权利」这一概念,来进一步证明他关于赤裸生命、主权、现代国家的关系的论点。我们固然可以这样解读霍布斯的观点,但是我们必须接受这种解读的结论:它实际上是政治的彻底消除(radical elimination)。一旦共同体内部的至高者不受任何阻碍,那么,政治必然消失不见。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把霍布斯的构想同马克思的国家消亡观念进行比较。虽然它们互相对立,但是就反政治后果而言,二者是相同的。在霍布斯看来,因为社会把法律赋予自身,所以权力集中在主权者手中是任何共同体秩序的前提。在马克思看来,因为无阶级社会实现了完全的普遍性,所以政治完全是多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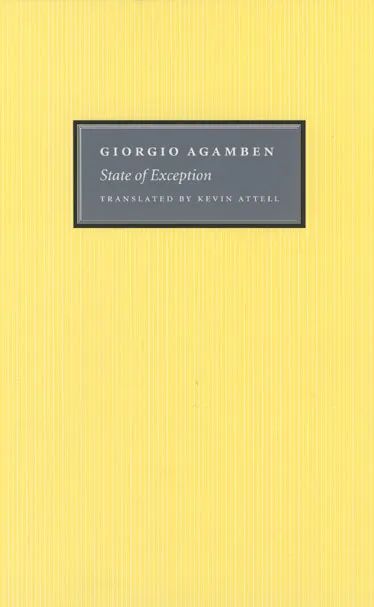
State of Exception / 图源: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但是,如果我们在霍布斯的图示中加入一些灵活性(souplesse),如果我们认为社会可以进行局部的自我规介(partial self-regulation),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社会的需求远远超出了赤裸生命的需求,而且赤裸生命具有任何至高权力无法忽视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但是,一旦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主权」就开始变为「领导权」。而在我看来,阿甘本恰恰掩盖了这个议题,因为他把「政治的彻底消除」(把社会纽带简化为赤裸生命的至高权力),当作一个政治性的时刻。 上文说过,社会的自我规介是局部的。我的意思是,社会和政治的需求来自四面八方,而不是单方面的。这意味着,社会需要不断地进行重新奠基(re-grounding)。上文说过,施密特认为,主权者的功能是建立法律秩序与更广泛的共同体秩序之间的一致(法律不适用于混乱状态)。如果主权者的功能确实如此,如果需求的多元性要求我们不断地进行法律变革和修正,那么,例外状态就不是例外的,而是社会纽带的政治构造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想要应用一条规则,需要第二条规则来细化第一条规则的用法。想要应用第二条规则,需要第三条规则。以此类推。因此,维特根斯坦得出结论,应用实例是规则本身的一部分。用康德的话说,这就是说,我们在社会纽带的建构中面对的是反思性判断,而不是规定性判断。维柯认为例外优先于规则的观点,也适用于我们的讨论。 正因为如此,我对例外状态的历史的看法,不同于阿甘本。在阿甘本的图景中,例外状态成为规则,意味着我们不可避免地滑向极权社会。而我对「例外」做了更一般化的解读,从而以更乐观的方式来思考我们的未来。上文讨论过罗马诺对革命法律的论述。不过,他的论述不仅适用于革命断裂的时期,而且适用于社会运动构成特殊政治空间、制定自己的法律(这种法律局部地在国家法律体系外,局部地在国家法律体系外)的各种情境。这种局部变革的分子式过程,对于力量的积累是至关重要的。一旦整个领导权格局发生更加彻底的变革,这些力量的潜能便会展露无遗。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可以提前看到,阿甘本的第二个论点也不成立。zoē和bios的区分,无法担负起阿甘本的历史解释中的关键角色。他在《神圣人》开篇说,希腊人用两个词表示生命:「zoē表达了一切活着的存在所共通的一个简单事实——活着。bios则指一个个体或一个群体的适当的生活形式或方式。」这意味着,生物不能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bios,一类是zoē——因为bios显然同样有zoē。因此,zoē主要是一个抽象物。哪怕只以繁衍生命为目的的oikos,同样有内部结构,同样基于功能的等级分配。因此,虽然oikos的目的不是政治性的,但是,它远不是赤裸生命,因为它有自身的构造和规则体系。这样一来,阿甘本的论点想要成立的话,就必须证明,在某些情境下赤裸生命不是抽象物,而是具体的事物。正是在这个地方,阿甘本让福柯的生命政治出场了:「根据福柯的说法,一个社会的生物现代性的肇始,是在那作为简单的活着的物种和个体,开始在社会的诸种政治策略中承受危险时。」最有启发性的地方是,阿甘本把福柯的生命政治与阿伦特的《人的条件》联系起来: 阿伦特分析过使劳动的人——以及,伴随它的那种生物性的生命——逐渐占据现代性的政治场景中核心地位的过程。在《人的条件》中,阿伦特把现代社会中政治领域的转变和衰落归结于这一点:自然生命的重要性超过了政治行动。
用这一番话来进行论证,可以说是以偏概全的。我们完全可以进行相反的论证:在现代性中,自然生命的重要性没有超过政治行动,相反,自然生命过去涵盖的范围逐渐政治化了。总而言之,把政治主权和赤裸生命截然对立的错误在于,我们假定,二者的对立必然意味着过分强大的国家的与日俱增的掌控。虽然「自然生命的政治化」意味着社会生活越来越多地受到人的掌控和规介,但是我们不能假定,这种控制一定发生在趋向极权的例子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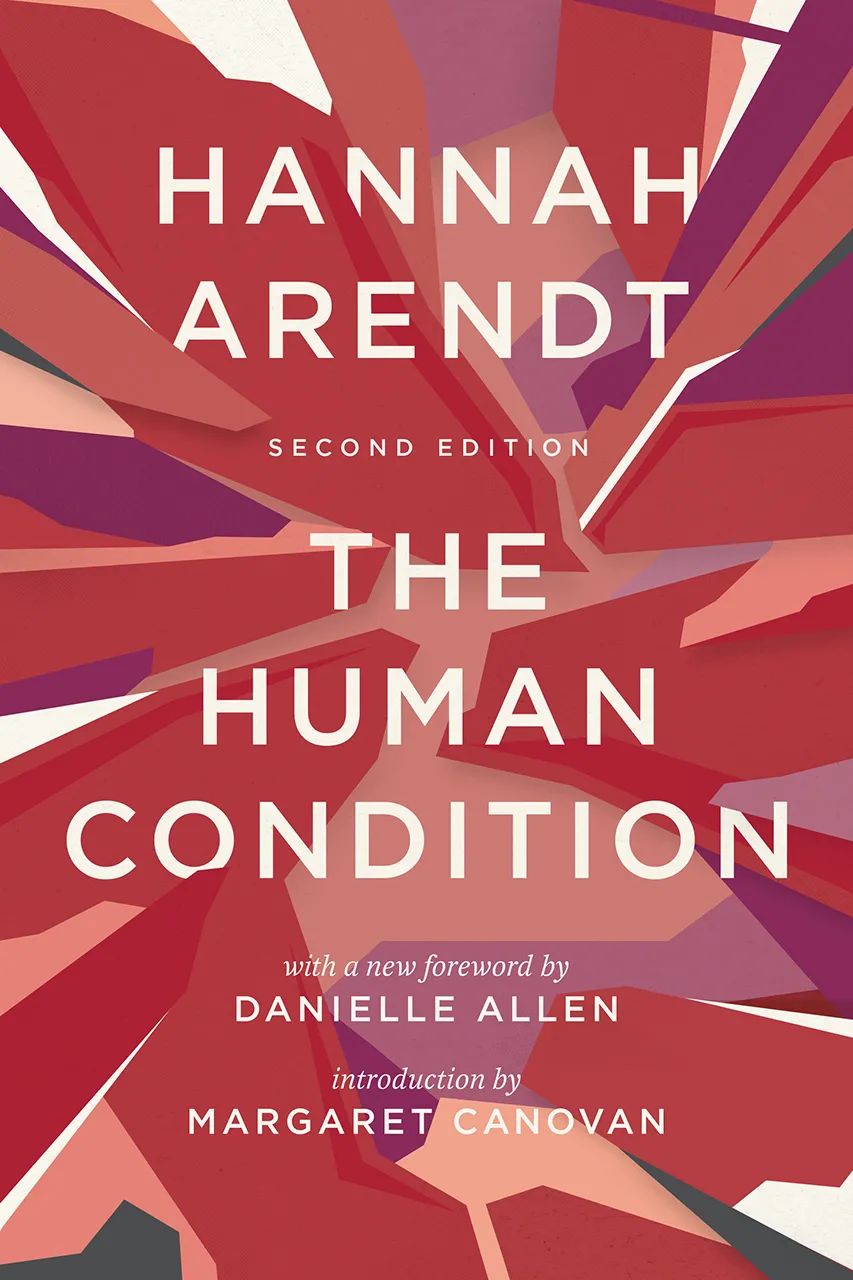
The Human Condition / 图源: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因为阿甘本认为禁止与主权有严格关联,所以,他肯定会设想这种趋向极权的例子。这么做的后果是,他混淆了各种不同性质的人的情境。上文说过,「赤裸生命」想要产生的话,禁止的对象必须是毫无防备的,完全服从至高权力的「弃置」。阿甘本描述的很多情境,实际上只是接近赤裸生命,实际上是政治干预的对象。 比如,他提到Muselmann:「羞辱、恐怖与惧意是如此彻底地夺走了他所有的意识与人格 ,以至于使他变为绝对地麻木呆滞。」再比如,他提到患有白血病的生化学家决定在实验室改造他的身体:「他的身体不再是私人的,因为它已被转变为一个实验室。但它也不是公共的,因为只有当它是他本人的身体时,他才能跨越道德和法律对实验所做出的诸种限制……他是一种bios,但这种bios在一个很特殊的意义上,是如此地将自身集中在它自己的zoē上,以至于无法与zoē相区分。」再比如,他提到凯伦·昆兰:「我们走进医院房间,凯伦·昆兰或者过度昏迷的人躺在里面,抑或,新尸体正在那里等待着被摘除器官。在这里,生物性生命——通过人工呼吸、动脉血液注入、血液温度调节而维持着机能——已然完全从以凯伦·昆兰为命名的生命形式中分隔了出来。在这里,生命变成了(或至少看上去变成了)纯粹的zoē。」 
zoē & bios / 图源:Medium 到此为止,阿甘本对赤裸生命的论述是合理的。可是,他后来把这种论述延伸到其他截然不同的情境中:从昏迷的例子直接跳到强盗的例子: 他的整个存在因如下事实而被缩减成一个被剥除所有权利的赤裸生命——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他而不犯杀人罪,他只有永远逃离或在外国的土地上,才能拯救自己……他是纯粹的zoē,但他的zoē本身陷入在至高禁止中,并不得不每时每刻应对它,寻找最好的方法来躲避或欺骗它。在这意义上,没有生命比他的生命更政治。
强盗或流亡者可以是政治性的,但是,他们的生命截然不同于凯伦·昆兰的生命,因为他们能参与对抗性的社会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强盗和流亡者有自己的法律。他们和城邦法律的冲突,是法律与法律的冲突,而不是法律与赤裸生命的冲突。阿甘本意识到,人们可能会批评他的赤裸生命的例子过于极端和边缘,于是,他用「一些也那么极端且更为人熟悉的事例」来回应这种批评: 例如,在奥马斯卡的波斯尼亚妇女便是生物学与政治之间一个完美的无区分界槛,抑或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的诸种军事干预。在这些军事行动里,战争因诸如营养或传染病防治等生物性目的而发起。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根本无法判断,我们的议题是什么:是关心人群的生存,还是把人民简化为zoē?在阿甘本的论证中,他不断地混淆这两个层面。强盗的例子已经说明,阿甘本的排除逻辑越界到赤裸生命概念的范围之外了。当他试图把主权/赤裸生命的逻辑延伸到一般的现代性理论中,这种越界就更明显了。首先,他指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人民」概念在大多数语言中是模糊的:它一方面指整个共同体,另一方面指较低阶级的成员。可是,他对这种模糊性的解读是,共同体剧烈地分化了,并且现代性的极权逻辑企图克服这种分化: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时代只是在不断地尝试各种方法以克服人民的分化,去激进地消除被排除的人民。这一尝试,根据不同的型态和视域,使右翼和左翼、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到一起,在生产一个单一的、无分化的人民这个工程上统一起来。
这种分析,是根本错误的。首先,分化与现状是完全相容的,因为社会多样性导致的差异不是以对抗的方式构建的。因为等级制度恰恰意味着社会分化,所以,对分化(多样性)的消除并不是统治阶级的系统目标。 其次,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对抗性的分化,讨论的是把人民建构为较低阶级的那种分化,那么,这部分人民肯定不会维持分化,反而会取代原来的分化。也就是说,部分试图取代整体,异质性试图融入新的同质性。因此,部分与整体、同质性与异质性的辩证法,比「分化的人民」、「无分化的人民」更加复杂。比起阿甘本这种机械的目的论,葛兰西的「社团阶级」,和「领导权阶级」,可以引发更加复杂的战略行动。差异既可以是总体内部的阵营,也可以是替代性的总体(它需要部分对整体的贯注,就像拉康的objet a)。同质逻辑既可以是完全极权的,也可以是解放性的,因为它把需求的多元性都关联在同一个等价链条上。主权既可以是极权的(它把权力完全集中在主权者手中),也可以是民主的(它是一种表达的力量 ,而不是一种规定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主权应该被视为领导权。 
由此一来,我们自然也反对阿甘本的第三个论点。阿甘本说: 集中营在我们时代的诞生,看上去是一个决定性地标示着现代性本身之政治空间的事件。它产生在这样一个时点: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系统——它建立于确定性的场所化(土地)与确定性的秩序(国家)之间的那个功能性联结上,由那刻写生命的诸种自动规定来调介——陷入了一个持久性的危机中,国家决定直接把照料民族的生物性生命作为它的妥切任务之一……一些东西无法在规介这种刻写的诸种传统机制中再起作用,集中营则是将生命刻写在秩序中的那个新的、隐秘的规介者。或者说,它是一个标明系统之无能性的记号——这个系统不转变成一个杀人机器就无法起作用。
这段天马行空的论述想要成立,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 土地、国家、刻写生命的诸种自动规定之间的功能性联合的危机,已经释放出「生物性生命/赤裸生命」这一事物。 2. 对这一事物的规介,由单一、同质的国家来承担。 3. 国家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它认为「赤裸生命」是可操控对象,认为其原型是禁止。 不用说,这三个条件都不成立。可是阿甘本——他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如何建构一种潜能本体论(ontology of potentiality)——用一种天真的目的论结束了他的论证。在这种目的论中,潜能似乎完全从属于预先给定的现实。事实上,这种目的论与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种「唯词源论」(etymologism)相辅相成。它们的共同后果是,导致阿甘本忽视了真正的问题——每一个新的情境所开启的结构可能性体系。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种可能性体系,那么,我们将会发现: 1. 刻写生命的诸种自动规定的危机,释放出的事物不只是「赤裸生命」。把这些事物都简化为赤裸生命,只是极端情况的例子,而不是现代性的潜在模式。 2. 社会规介过程涉及多种多样的例子,不是国家能够涵盖的。 3. 现代性中的国家建设过程,涉及复杂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的辩证法,不是集中营范式能够涵盖的。 阿甘本把现代政治建设的整个过程都统一到集中营这个极端和荒谬的范式上,这种做法不光是讲述了一段歪曲的历史:而且妨碍了我们探索现代的遗产所具有的解放潜能。 唯有在有可能超越任何法律的概念(甚至法律的具有效力但无意义这一空白形式)来思考关于弃置的存在时,我们才能走出主权的悖论,走向一种不受制于任何禁止的政治。一种纯粹的法律形式唯是空白的关系形式。但空白的关系形式不再是一个法律,而是法律与生命之间无可区分的一个地带,即一个例外状态。
阿甘本没有告诉我们,「走出主权的悖论,走向一种不受制于任何禁止的政治」意味着什么。但是,阿甘本不需要告诉我们:问题本身的表述,已经包含了它的答案。摆脱任何禁止和主权,就是摆脱政治。「完全和解社会」这一神话,支撑着阿甘本的政治(非政治)论述。而且,这一神话导致阿甘本抛弃我们的社会中的所有政治选项,把它们都统一到集中营这一宿命上。阿甘本不是解构政治体制的逻辑,展现可能产生斗争和反抗的领域 ,而是用本质统一(essentialist unification)提前关闭了该领域。政治虚无主义,就是阿甘本最终的讯息。/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Philosophia 哲学社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备战深国交网”除发布相关深国交原创文章内容外,致力于分享国际生优秀学习干货文章。如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原谅,并联系微信547840900(备战深国交)进行处理。另外,备考深国交,了解深国交及计划参与深国交项目合作均可添加QQ/微信:547840900(加好友时请标明身份否则极有可能加不上),转载请保留出处和链接!
非常欢迎品牌的推广以及战略合作,请将您的合作方案发邮件至v@scieok.cn本文链接:http://bpc.scieok.cn/post/2571.html
-
<< 上一篇 下一篇 >>
拉克劳论阿甘本:赤裸生命以及主权的不可决断性 / 翻译
26202 人参与 2021年11月28日 21:22 分类 : 深国交哲学社 评论
search zhannei
深国交2024年英美本科录取小计
-

未标注”原创“的文章均转载自于网络上公开信息,原创不易,转载请标明出处
深国交备考 |
如何备考深国交 |
深国交考试 |
深国交培训机构 |
备战深国交 |
联系方式
Copyright www.ScieOk.cn Some Rights Reserved.网站备案号:京ICP备19023092号-1商务合作
友情链接:X-Rights.org |中国校园反性骚扰组织 | 留学百词斩 | 南非好望角芦荟胶 | 云南教师招聘考试网 | 备战韦尔斯利网| 备战Wellesley



